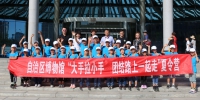纯文学期刊《天山》25年后复刊
复刊后的天山封面
《天山》1986年1-3期合订本
《天山》1988年第3期 图/市作协提供
新疆网讯(记者李卿报道)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席卷全国,纯文学期刊成为文学发展的最主要阵地。在新疆同样如此,1980年由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办,市作协创刊的《天山》就是当年最红火的纯文学期刊之一,当时热爱文学的青年从在《天山》发表小说、诗歌开始,踏上文学之路。可以说,《天山》承载着新疆一代人的文学记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疆文学盛景的一个侧面。
但不到10年,《天山》就因一些原因遭到停刊。直至本月19日,才终于得以复刊。停刊25年后,《天山》再次回到乌鲁木齐的文学视野。21日,《天山》复刊后的第一次座谈会在首府举办,虽然曾经的文学青年都早已青春不再,但关于《天山》的记忆,却清晰如昨。
创刊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1980年《天山》创刊时,如今的新疆作协副主席董立勃还在上大学,鲁迅文学奖得主刘亮程还在他的小村庄里当农民,散文家黄毅才不过19岁,周军成才刚刚开始写诗……谁能想到,这些人都将陆续在《天山》发表作品,并且一鸣惊人。而之后一两年,董立勃更成了这家期刊的责任编辑。
彼时,文学热席卷全国,新疆自然也不例外,《天山》以及《边塞》《新疆文学》等是新疆最初的几家纯文学期刊,按照董立勃的说法,也是当年最重要的几个文学阵地。许多热爱文学的人都将自己创作的作品投来,一时间,百花齐放,新疆文学界一片繁荣的景象。
董立勃回忆说,他1981年上大学时就在《天山》上发表过作品,还参加了不少《天山》举办的文学活动,“我这个文学青年的成长,和《天山》有着密切的关系。”之后,因为《天山》缺少专业人才,董立勃才从克拉玛依调回乌鲁木齐,担任《天山》的编辑。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编发的第一篇稿件就是自己约来的苏童小说《云阵》(又名《一朵云》),当然,此时的苏童还远未出名。
和董立勃一样,黄毅对《天山》也有着极深的感情。当年的《天山》为单月刊,投稿者众多,篇幅也十分有限。董立勃担当责任编辑后,对文章质量的要求也非常高,一篇文章能发表在《天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1986年,黄毅的作品被刊发了,而且是占篇幅很大的一组系列长诗,“显得相当有分量,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黄毅回忆说。之后这首组诗又被新疆电视台看中,改编成电视诗集,很快又在全国获奖,黄毅从此成名。
同样,周军成的成名也得益于《天山》。他80年代初开始创作诗歌,1987年《天山》发表了他第一首诗。诗发表之后,周军成一夜成名,很多人找到他家里拜访他,和他探讨文学创作。“当时特别有荣耀感,”周军成说。
据董立勃介绍,当时的《天山》对新疆文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力巨大,全国都很知名,甚至堪比国内几家著名期刊,“很多新作家的起步都是从这里开始。一本刊物就是一个文学的园地、摇篮。”正像《天山》复刊号主编熊红久在复刊第一期的扉页上所言:“《天山》承载了多少文学青年的理想与梦境,也改变了多少志士才俊的人生和命运。”
停刊
曾驱万马上天山,风去云回顷刻间
可惜好景不长,从创刊开始不到10年,《天山》就遭停刊。
80年代末,文学热潮逐渐消退,社会转变。国内也开始了一轮新的批判浪潮,很多刊物都受到冲击。“当时大家都想挣点钱,搞通俗刊物,发行量很大,结果搞得质量每况愈下,用现在的话说,叫低俗。于是很多期刊都成了清理对象。”董立勃说。
但这并不是《天山》遭停刊的主因,虽然《天山》也被点名批评,但情况并不严重。“错就错在态度强硬,”董立勃回忆说,当时被批评,但主编觉得自己没错,不愿意承认错误。
当年往事,如今已作笑谈。就这样,创办10年,留下了一段新疆文坛的故事和记忆。
“《天山》复刊了,本月19日出第一期。”
“你终于把这件事做成了……”
这段对话发生在熊红久和新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陈漠之间。21日的座谈会上,陈漠谈及此,显得十分感慨。而黄毅更坦承,自己拿到25年后《天山》的复刊号,竟有些热泪盈眶的感觉。“当年我还不到30岁,现在已经成了老头,岁月和青春都跑哪去了?”
复刊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
《天山》能够复刊其实并不容易,25年来,陆陆续续打了不少报告。最后一次,熊红久写了很长的报告,列举了全国省会城市的刊物,唯独乌鲁木齐没有。最终,得以批准。略微遗憾的是,由于没能申请到刊号,《天山》现阶段只能作为内部刊物面世。
不过,《天山》复刊第一期的内容显得相当有分量,董立勃、沈苇、郁笛、王族等新疆著名作家都有新作在此发表。而如今双月刊的《天山》发行量达到4000册,读者群主要为社区居民、各大院校文学爱好者及作协会员等。据董立勃说,4000册的发行量已经达到省一级纯文学刊物的水准。
熊红久则说,新《天山》将立足于乌鲁木齐市,挖掘本土作家,文章内容则要反映新疆本土生活,做到宣传正能量,提升人们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建设家乡的热情。当然,熊红久也保证,尽可能维持期刊的质量,做到文学性和宣传性的平衡。除此之外,《天山》还计划开展评奖活动,每年评出最佳小说、诗歌、散文各一篇,以此来鼓励创作。
无论如何,承载一代人文学梦的《天山》终于得以复刊,正像陈漠所说,很多事物都有休眠期,人也是一样,要积累能量,要调整生理和心理,休眠了25年不一定是坏事,也许是为了积攒更大的能量,在2014年末爆发,闪现更耀眼的光芒。
“叫复刊或许不太合适,应该是‘醒刊’。”陈漠笑着说。
其实不难发现,也不可能忽视,复刊后的《天山》,依然面临一些困境。比如,没有刊号即意味着刊物没有户口,没有广告发行权,没有订阅邮发权,不能在书店销售,也不会被图书馆收藏等等。
也许这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期刊本身。纯文学读物愈发式微的今天,《天山》这样的期刊真能够办起来吗?对此,黄毅直言不讳:“《天山》应该做成给搞文学的人看的小众读物。”在栏目设置上,要向《山花》《天涯》等杂志学习,开辟一些独特的栏目,以此提高自己在文学界的影响力。如此,即便没有刊号,也能做出品质来。
《西部》杂志副总编张映姝则担忧《天山》的稿源问题,“复刊第一期均是新疆一线作家的作品,质量可以保证,那么以后呢?将如何保证期刊的稿件品质?”董立勃也指出,即便是成名的作家,其作品也不可能每一篇都好,若约稿质量达不到标准,发还是不发?如果不发,难免会得罪人,再约则不易。如果发,这个口子一开,杂志难免沦为人情产物。这个问题该如何把握?
熊红久对这样的问题均有过考量,但现阶段均难以完全解决。除了这些,熊红久也承认,刊物刚开始发行,机构和编辑人员还没有完全到位,刚开始和有编辑能力的文化公司合作。不过,熊红久也显得信心十足,他相信这些问题随着办刊人员和专业人士陆续到位,都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座谈会大厅墙上挂着的一幅画,一群骆驼负重蹒跚前行,上面写着四个水墨大字:任重道远——《天山》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