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修复师:跟文物在一起 生命被延长了
钟表组王津、亓昊楠师徒 图/梁辰
模糊又高级的快乐感
《我在故宫修文物》摄影师张华在故宫文保科技部呆了4个月,见到的王津永远是:衬衫干干净净,领子立得直直的,裤头附近的衬衫掖得严严谨谨。他问过王津:您是当兵的吗?王津说,没有。
钟表组的木门总紧闭着。王津说,开着门不行,太脏了,尘土飞进来会影响机械运转。还有柳絮跟雪花似的,落得哪哪都是,跟煤油搅在一起,多了就脏了。受限于故宫古建保护,文保科技部不能像国外修复室一样装上防尘门、除尘管道设计。
你感觉不到屋内有人——实际上有4位师傅正在忙活。王津的徒弟亓昊楠正低头清洗一个18世纪的铜镀金嵌玛瑙规矩音乐表——顶部有个小圆钟,底部是首饰盒,插着剪刀、梳子、耳勺挖……他把清洗好后发着淡淡金光的小玩意排成一列,放置于一银色不锈钢盆内。中国古代器物大多成双成对,他和王津一人修一个。通常用煤油清洗机芯、鎏金器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稍刺鼻的煤油味,源头是王津桌旁一只装煤油的老式黄色搪瓷面盆,反盖的盖子躺着一只钟铃。王津指着清洗好的几只小神象说,“看,那时的鎏金,洗了就这么亮。”
王津演示工作状态:抽屉往外拉,身体往前倾,手里的古物即便掉也是掉进抽屉。桌子前方被白色的木板挡着,防止零件飞出去。他不戴手套,橡胶会跟煤油起反应。他右手边有个电话,几乎不响,对面的两台电脑也没人碰。偶尔窗外有乌鸦呱呱叫。师傅们都低头干活,不说话。王津说,也不孤单,干活怎么会孤单呢?没事干才无聊呢,坐在那多孤单。没有工作计划,也没有领导催着,想干的时候自然就去干了,偷懒没必要,不存在其他诱惑。亓昊楠低着头,经常是膀胱有点涨,抬头一看,11点了,该吃午饭了。
导演叶君形容这群人像树懒,但不是动作慢,是另一种慢:比如第一天进故宫拍摄,铜器组王有亮在磨一把青铜剑,影子倒在窗户上,全身静止,两只手反复来回擦一个位置,“两三个月还在擦,一直在擦。”有时他们看着钟表组的王津自己做螺丝,一点点儿锉,锉上两个小时。钟表前的小木门有个小缝隙,他得花三四天解决。
故宫钟表的功能主要不在计时而在装饰和表演——这里头的门道就深了。精确最重要。比如他修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一层就五面,每个面上有不同的功能在转,零件固定在底下的木座上,时间长了就会收缩或者变形。齿轮的咬合就差那么一点点,它就不转了,要调试。轮跟轮之间调试好,还要咬合,一点不能差。王津说,调试钟表不能凑合,没法凑合,糊弄它肯定就搁停了。还不能轻易下手,稍微动错,恢复起来就更难了。耐性都是磨出来的。王津也会急,急了,他就不干了,再干有可能还出篓子,就先上周边转转。等心安了,接着干——他的师傅这么教他,他这么教亓昊楠。
王津今年55岁,个子瘦高,站立时双手叠放在身前。他说话温雅,有些害羞,采访时双手反复搓着那副金色细框眼镜的眼镜腿。他的专注力极高,一秒也不会走神,逻辑清晰,像钟表内精密的发条,这不只是出于礼貌,也源自职业素养。亓昊楠说师傅从不发火。跟着师傅两年,他在热闹的地方也呆不久了。师傅在他眼里一点不显老。办公室的姑娘在一旁笑:这师徒可是我们科技部的颜值担当。
16岁那年,因祖父在故宫图书馆工作,王津有机会进入故宫。头天报到,老厂长领着他到各科室转一圈,问他:喜欢动的东西还是喜欢静物呀?他走进暗哑的钟表室,案子上的一盏台灯照着一个铜镀金的座钟,师傅拧好发条,这钟里就传出了音乐,还会动。师傅挑徒弟时,马师傅看他岁数小,就留下了。没有仪式,马上开干。起初他只能在非文物上练手,把两个残破的小闹钟反复拆,拆完了装,装完了拆,再清洗。练手一年,才开始碰文物。马师傅不太严厉,徒弟活怎样他心里有数。
当年的故宫比现在静,整个北京城也静。外地人进京还得登记。王津家在故宫南面的景山东门,每天走路上班。那会儿故宫门票才一毛钱,游客也很少。当时故宫跟景山公园隔着的马路还没有铁栏杆,也没啥车。夏天,王津中午在故宫吃完饭,先去什刹海游泳,再回来冲个澡,继续上班。冬天就出去滑个冰。
1982年王津离开师傅到广东省五羊博物馆修了一座钟,此后就独自干大活。2009年轮到一座有相当难度的 “老人变戏法钟”。这钟不大但很丰富:有音乐,有小鸟叫,还有转花,花朵中坐一小人,人的头发、眼睛会动,一手拿一小碗扣在桌子上,手一抬起来,底下是一只小鸟。扣上打开,底下变成4颗小红豆,扣上再打开,变白豆了——靠几根拨片,这一切就活了。当时里面零件几乎坏了,杆子折了,小鸟交换的气囊全被虫子咬烂。大概研究了一年多,王津和同事才让小鸟复活。跟其他钟表一样,没任何文献可参考,师傅们反复看着大钟,凭借对机械原理的理解和想象力解决问题。
故宫有1500多件钟表,王津修过两三百件。剩下的钟破损程度很严重,也更费工夫。王津说,再难,也没有修不下去的钟,难点就是慢点,一点一点琢磨。他从不同时修两个钟,一个个来。遇上复杂点的钟,修上个半年是常事。因为现代技术的保护,多数钟也就有点小毛病。一辈子赶上一件能大修,他很珍惜。
花一两年功夫,一群玩意在眼前活了,这种征服感王津很熟悉。2007年,他和朋友自驾进入川藏北线,隔数十公里才有一个小村,路实在太陡太坑坑洼洼。夜晚,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上的星星很低,四周是黑压压的小山包,特别静。大家都觉得太难了,车最后还是开到了珠峰顶,远处日光照着雪白的珠峰顶。他说他没法形容当时的感受。在三十平不到的小屋里,日复一日,他获得的也是日常语言所不能描述的模糊又高级的快乐感。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
2016年春季,《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大红。铺天盖地的公众号在赞美一群故宫文物修复者,在纪录片制片人程博闻看来,这是大众的一种自我投射,“是我们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你就觉得他们特牛逼,一辈子就心无旁骛做了这么一件事。”程博闻说。
这是历史上首次有摄像头对准故宫的修复部门——一个静谧的“农家院”:树很多,樱桃树、杏子树、枣树……地上跑的有土鳖、壁虎、黄鼠狼,传闻还有狐狸。天上飞的有喜鹊、乌鸦、鹰。人与环境合一:王津的手有股淡淡的煤油味,铜器组师傅手上则有锈。张华想,要是换在写字楼里,人的状态可能完全不一样。“在这样的大院,临摹组的师傅才能体会到作者下笔时的心情、触感。”他被师傅们工作的质感吸引,“特别美。”
“闯入者”多少给这里带来了骚动。采访到一半,一位姑娘走进屋来问,“王津老师,跪求您签名啊,我都给推了三次了。”王津害羞笑笑说,待会吧。“经常有人找你要签名吗?”“没有,很少,肯定都是小孩。”
最近他坐103路公交上班,俩陌生人冲他来了个“迷之微笑”。坐飞机去重庆,有空姐送枕头给他。王津还奇怪,为什么外头人人吵着要给他当儿媳妇,都没问一下他是否有儿子……但他也有冷幽默,“这下我找儿媳妇好咯。”
在王津看来,没人关注是正常的,“普通的工厂工人,不也没人关注吗?不也自己干自己的吗?”故宫老一辈的艺人大多如此。比王津年纪大些、皮肤黑、表情有些凶的木器组师傅史连仓3岁的时候就住在故宫边上了。父亲在1982年从故宫木器组退休,他进入了木器组。五十多年的时间就从故宫流过去了。在临近拍摄结束前几个星期,即将退休的史连仓跟摄影组讲起小时候吃过故宫的野菜。他一辈子都贡献给了故宫。然后两分钟没说话,眼泛泪光。大家也不吭声,静静等着。
5年后王津就要退休,他准备返聘。他对外界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年轻人一直跳槽?做一件事不是挺好的吗?钱对他而言,够吃够喝行了。工作桌旁放着一堆《名表》杂志,十几年来他经常参加各种展览。收藏圈过分商业,他没多大兴趣。外面钟表一生产就一万个。故宫的钟,一辈子只能见一次,修好了就进库了。他指了指旁边放着的一个待修的铜镀金乐箱水法跑人双马驮钟,“这在市场上,值个过亿吧。”
程博闻有过问号: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会不会很乏味?他后来想,只做一件事,一个人拥有的诚心,很可能跟他第一次做这个事一样。他不再依赖花花世界,“有他自己的幸福感。”
想到库房里还有数百个钟没有修,王津心里着急。“如果都修好了该有多好啊,起码我能看着啊。”采访中王津反复说,自己看着高兴就行了。那个大男孩在16岁找到热爱的大玩具,40年后,能跟人分享,他同样高兴。
《我在故宫修文物》拍摄临近结束,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还差些没修好,王津跟摄影组说,他希望能尽快完成,让这座钟能留在影像中。不然,他自己也不能再看见它了。后来他做到了。王津说,他希望未来每修好一件就能录一个视频,观众手机一扫码,就能看它活过来。
有那么一刻,我能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珍贵。当时我们身后传来一阵异常清脆的铃声——来自一座刚修好的大钟。王津说,靠现在的技艺,很难复制出同样的声音——钟铃的材质不是纯铜,制造工艺失传了。“真假完全能听出来,假的就没那么清脆。像这种小钟铃,基本上做不出来了。”
他拿起黄色搪瓷盆上的银色小音铃,“这绝对不能掉地上。这钟铃特别脆,跟敲瓷器似的,掉地上就跟小瓷碗似的,一摔就成好几瓣。”然后用一根针状的工具在小音铃上轻敲,发出一串清脆的小调,最后一声“叮……”他右手轻轻往外拉,做侧耳状,“你听,特别长。”他又敲,“Do Re Mi Fa So La……”
这东西你琢磨过吗?
跟王津轻松在故宫生根不同,生于1978年的屈峰曾用了两三年时间逃离故宫高墙。在逃离情绪最浓烈的2009年,他创造出了两个雕塑:一个叫《云翼》,小人身上背着一朵云,飞起来了;另一个叫《木偶的游戏》,一木头人手里拿着一木头在雕——意指他自己是一个木偶,玩的也是木偶。
“我不甘寂寞,我不愿闷下头来一辈子做匠人,我想把事情做得风生水起,被人看见。” 文保科技部木器组组长屈峰眉毛紧蹙,用极快的语速说道。对屈峰来说,故宫匠人的工作更接近复制古人的创作,缺乏自我表达的空间。程博闻理解屈峰:“匠人”精神如今在国内备受吹捧有个时代语境——人们太过浮躁——这也是纪录片大火的一个原因。
挤在游客群里的人很难体会到,一踏入故宫西北角的文物科技部,人就被一股冷气裹住(冬天的故宫比外面低3度)。故宫的女生大多手脚冰凉,常讨论谁掉的头发多。但跟屈峰粗犷的气质相称,木器组的环境有着蓬勃生气。隔壁组女生多,所以木器组的WIFI取名叫“你们心目中的男人”,“如果蹭WIFI,呵呵。”门经常敞着,正中搭了个棚,种过南瓜,接下来准备种葡萄。一只小野兽蹲在门右侧——由一个树根、石兽头还有两只生锈镰刀组成。花盆里种了玉米、西红柿,靠门左侧有个鱼缸。两灰一花3只猫被训练得永不进屋。屋内杂乱:墙上挂着史连仓父亲和其他文物修复者的黑白合照,角落堆着大大小小的花盆、书刊杂志,窗边挂一串干葫芦。一块紫檀嵌玻璃画插屏屏帽碎成几十块,被放在不同的工作桌上。
巨大工程刚开始,“你看这墩,一共7个,现在少了3个,得复制出来。你看,这碎的,跟拼图游戏似的。现在不好看,组合起来就好看了。你看,鱼纹、蝙蝠,还有个寿字。”屈峰说。修好的文物漂亮,比如一把立在砖地上的红木蝠寿万代椅,透着红光。
年底,他们会搬到故宫西边城墙边的新办公楼——更现代化,更科学。“只有植物留下。”全院人不舍。
——他从农村来的,对那些植物动物不觉稀罕。签三方协议那天,他在门口窄巷子徘徊了一小时。他热爱当代艺术,专业成绩又是最好,这份工作意味着他要放弃当艺术家的梦想。但在故宫工作毕竟稳定,有基本收入,提供户口。毕竟一些美院雕塑系毕业的同学,至今还在798艺术区里打拼。
屈峰粗眉细眼,性格火辣辣、急冲冲。年轻时留着长发,因为热爱艺术,从西安费尽艰难考进北京。他说话耿直,内心细腻,糅杂了江湖气和学者气,科技部人称“屈大侠”。有时他觉得摄影组的问题弱智,直问:之前你经过大脑考虑吗?
他在文物面前很慢,被逼的。刚进故宫不久,他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一下做完了,师傅说,你做快了。屈峰问,做快了不好吗?师傅说,这东西你琢磨过吗?屈峰愣住。
这10年他最大的获得是磨性子,对着文物静下心所需时间从一小时减少到20分钟。“这家伙就是一个死的,不管你怎么着对它,它都那样,最后你就干脆算了,你这样我就这样咱俩耗,这就是一种修行。”
屈峰爱琢磨理论,文物科技部的老师傅却大多因“文革”错失了高等教育,这让他有些孤独。最不适应的是,他着迷于想象力和创造性,修文物却必须严格按照规律来,“有时是一种限制。”木器组修复的大多是实用性家具,有些审美价值不高。有时他看到一件家具,“很丑,老想给它改了,老有那种冲动,理智告诉我这事你不能干。一个丑陋的东西,你每天还得按照它丑陋的方式给它修复。直到慢慢接受,丑陋也是一种存在。”他最喜欢看的是书画,常隔着距离围着修复古书画的人看,或在雕塑馆转悠。
起初的待遇也让家境一般的屈峰沮丧。当时他在望京租房,6点半起床赶班车,他总赶不上,老打车,月工资一千四百多,根本不够花。
大部分人不能一下适应故宫封闭、孤独的气场。摹画组巨健伟刚到故宫时,只能磨墨。又花整个月,学画一条竖线。木器组谢扬帆第一份工是严格按照尺寸要求,把木头刨平,做成大小中号3个刨子。他承认刚开始有点躁,“憋着鼓劲,老想用劲但又不敢使大劲。”
我从一位同行处听说,故宫是京城非常难打交道的机构——程序繁琐,非常严谨。叶君本打算做动画扫描,结果扫描文物的审批递交后7个月也没下来。刚进入这个院子,我确实感到有点憋。这里有故宫惟一一道电子锁。记者和摄影师被告知不要分开行动。为保护文物安全,采访时两位办公室的姑娘在一旁陪着。
文物修复者的工作流程严谨谨:提取文物前需要一连串手续,再研究文物伤况,做实验、拍照、记录、化验、进一步论证,再试探性地去修。“累,烦琐,就是烦琐,你老是这个流水作业。尤其你要是干旧活,天天一个样。你要是经验不丰富也麻烦,还有寂寞。”书画修复组的徐建华对叶君说。
屈峰有时听外面朋友聊股票:哎呀,简直天方夜谭。他一说文物,对方觉得还不如聊股票。
今年4月,作为科长面试新一拨年轻人,他给毕业生提醒:你们知道这个工作性质吗?想过自己的性格合适吗?一位年轻人说:“一想到每天都能接触文物,就心潮澎湃!”屈峰说:“这个地方可不能澎湃,一澎湃就麻烦了,还是要冷静。”
王津那一代人对工作并无太多选择,但对故宫的中生代而言,时代是另一种面貌——经济蓬勃,世界花花绿绿,多元的价值观极具冲击性。即便如此,他们大多人也在故宫呆了10年左右。程博闻经常问他们:没想过要离开吗?多数答案是:在故宫前5年,每个人内心都很挣扎,他们不断自我对话,再自我和解。
纪录片中,屈峰有一段话被剪掉了:他希望外界不要特殊化故宫文物修复者,“外界把我们想象成超人、非人,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我们也是人,也要吃饭,要面对经济压力。”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是高危行业,“绝绝对对高危。”“本来可以得心应手的问题,到了一级文物身上,恰恰是由于它的‘身份’,你反而没把握。你会双手颤抖。问题是,有些东西永远不碰不行,我们只有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去(把握)。当这种压力变大了,很多人不就宁可不动它。现在形成这种慎之又慎(的风气)。外界有没有想过我们承受着这样高危压力,谁给我们买过高危保险呢?”
慢与快,守与破,并不对立
2009年,屈峰整整反思了半年,想通了:他留在故宫,把自己看成学者而非匠人。老前辈说文物修复靠感觉,但屈峰研究其中学理,介入到文物修复的理念:每进来一个文物,他和同组人都先激烈辩论,文物要保留的到底是什么,再制定修复方案。比如某个文物破了个口,影响它最重要的审美价值,那补还是不补?他不希望修复文物只按传统套路——体现人的价值,“复活的意义,是要了解当时的时代审美是什么,格物格物,物是人创造的。传承文化,要传承这个。”
这些天他琢磨一把黄花梨六方扶手椅子:从构成关系上讲,它变宽,一宽就显得不好看了,空荡荡的,但是,它又有个办法把这个“空”给破掉了,它的横截面就跟梅花儿式的六瓣。一下子不空了,丰富了。屈峰为这张同时具有儒学价值和高标准美学的椅子写了一篇论文,“为什么只是出现了几把?因为材料缺失呢?还是其他?”
红墙内的日子不像过去那么呆板单调了,屈峰逐渐找到自己的天地。去年他给故宫院长单霁翔写信,建议成立一个雕塑研究所,院长批了,他挺高兴。
他显然有自己的理念。比如故宫修复恪守修旧如旧的原则,但在屈峰看来,“什么叫旧,你界定了旧你再谈修旧如旧,对不对?历史的痕迹要不要?比如说《芈月传》摆了很多锈了的青铜器,绝对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当时的贵族会给家里摆一对生了锈的东西吗?有人认为残缺是美,但有的残缺真的不美。你进了故宫,红色的墙上掉下来几块墙皮(漆),你会觉得它美吗?但故宫古建上的彩绘可能有一些破旧,你在原来基础上把色彩补一下。”屈峰认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以日本修寺院为例,日本隔3年就把这些寺院全拆了,重建一个,它的修建观念是另一种认识观——保留的是技术。
戾气渐渐消化,2009年他的作品“云翼”也在一个展览上被香港一位藏家买走。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屈峰有个小小的工作室,他没停止自己的创作;也有个热闹的艺术朋友圈,在雕塑圈内有些名气。
在程博闻看来,故宫的慢和外面的快,匠人工作的守和艺术创造的破,对这些师傅而言并不对立。“这么多年,他们内心肯定找到了平衡点,才是现在这个状态。真正的大师一定接受所有,有海纳百川的力量。”正因如此,摄影组能走近他们,大家也才那么喜欢他们。
纪录片里有不少师傅们出宫的镜头,脱离狭促的拍摄空间,风吹进大巴,他们的脸上添了放松、洒脱之意。
古典梦想
在故宫拍摄的4个多月里,出生于1989年的夜猫子程博闻每天5点半起床,从南四环花一个半小时骑自行车到故宫。叶君则从城西骑过来——好几条裤子给磨破了。拍完纪录片,他们也跟故宫的年轻一代修复者一样,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
80后成长于中国经济急速增长的时代,家境殷实让他们在人生选择上可以实现更多自我意志,但自由往往意味着在选择面前陷入焦虑。通常有两类工作吸引程博闻的同龄人:一是能经常出差,接触各类不同的人。二是能一夜暴富。程博闻属于前者,喜欢到处飘,完全安静不下来,“人生不就应该让自己爽嘛。”
但他们到了故宫,看到一群年轻人安静地在干活,抬头跟他们打招呼,“嗨!”到了中午,大伙齐齐埋头睡午觉。程博闻尤其记得其中二十多岁的周健翔,个子很高,脸上不太有表情,只是低头细致地干活。周末在外面学满文,“在故宫工作能用到满文的地方就是匾牌吧。”
大多数年轻的文物修复者是毕业于艺术院校的优等生,他们喜欢对人生进行思考、自省,想要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想要找到自我存在的意义。跟这个国家其他文艺青年群体相比,他们少见地热爱中国传统艺术,葆有古典梦想。
纪东歌高考前就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读中央美院的文化遗产专业。跟北京每个小孩一样,她对故宫的红墙绿瓦有情结。她第一次去故宫是两岁,记事儿是6岁——回忆里有“建极绥猷”(太和殿)和“正大光明”(乾清宫),细腻的香灰砖。珍宝馆里的玉器珠宝非常精致,小女孩眼前一亮。长大后,纪东歌日复一日,每个黄昏骑自行车路过太和门广场。
刚做妈妈的纪东歌微信接受记者采访。她形容自己“比较独,从小喜欢自己思考,喜欢传统,比较固执”。作为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的父母支持女儿的选择。后来她在北大文博学院听课时,接触到上海的陶瓷修复高手于爱平老师,主动拜其为师。后来她又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陶瓷考古与研究专业研究生。她太清楚自己的性格了,像上海师父一样做修复,收入会比在博物馆或研究机构高很多,但她宁愿在博物馆做一名修复工作者兼研究人员。她就喜欢单纯的环境,不用考虑物质或名利干扰,单纯面对文物。没什么比自我价值更让她快乐。
镶嵌组的罗涵也对自我有着清晰认知。本科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珠宝鉴定专业,她对中国古代玉石的兴趣源于一门古玉鉴定的课,“西方以审美为主,但东方会把人的品质比作玉,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你要像琢磨玉石一样打磨自己,把自己变成更优秀的人。”后来在中山大学读研,她对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和广州南越王墓的玉衣片进行检测分析时,再次被汉代古玉的精美工艺强烈吸引,“特别大气磅礴。”进故宫工作的愿望自然发生——从事古董珠宝研究和评估,没有比故宫更合适的地方了。
罗涵一头利落短发,大眼睛高鼻梁,举止间有股侠义之气,拍照时她笑嘻嘻问摄影师:我帅吗?对于人情世故,她心思并不复杂,穿嫩粉色皮衣是因为保留了纯真而非自恋。她的微信头像是国产动画的小怪兽比丢,朋友圈很少转艺术之外的内容——最新一条是匈牙利女摄影师Little chipiee的作品《You live only in my memories》。
这份工作多少让身边人难以理解。同学们叹息她可以去珠宝行赚更多。父母希望她在离老家福建更近的广东工作。
为杂志拍照前一天,罗涵翻了一整晚衣柜,精疲力尽,一无所获。她心里泛起少有的失落感。然后她在一件嫩粉色皮衣和淡棕色皮衣之间踟蹰,皮衣帅酷,是她的风格,但颜色太休闲。她承认,这样的时刻,自己会羡慕那些从事珠宝商贸年薪数十万的大学同学。月薪几千,她没法在衣服上花费太多。在故宫文保科技部工作,年轻人穿得最多的就是一件靛蓝色的大褂工服,或者是系一条右侧印有红色字体“故宫博物院”的黑色围裙。
故宫附近最近地铁到文保科技部也需要25分钟路程——这对每个年轻人都是噩梦。木器组的谢扬帆听了学长的劝告,第一年就买了辆摩托车,每天骑摩托车到地铁,再转公交到故宫。艺术青年习惯熬夜,前半年他根本起不来,特别困。但外地年轻人想留在北京,故宫有它的优势:工资不高但解决户口,还能有美学沉淀。
谢扬帆也有过跟学长屈峰一样的适应过程。跟屈峰一样,谢扬帆以前是留过长头发的艺术青年,刚开始会着急,做雕塑做躁了,啪,就扔了,砸了。现在不行,有责任了,得谨慎、得慢一些。在故宫两年,他显然适应得不错,这可能跟他本身稳重、温和的性格有关。在他看来,故宫工作是跟外面不同的一个体系,给予他平衡的力量。从视觉上来说,他在故宫里外来回切换,也不会感觉到疲劳。思维主要是慢、谨,而当弦绷得久了,他也偶尔搞点创作。
不惧未来
刚进镶嵌组时,罗涵反复练习把贝壳磨成片料,学雕刻能力,再学镶嵌技术中关键的粘接程序,包括传统胶粘剂的熬制、配比和粘接手法。罗涵用手指圈了个硬币大小的圈,“我修过一个很小的如意嵌件,上面的小珍珠才0.3毫米,非常多,往上粘眼睛根本受不了。”因为使用手柄式玉雕机,她的手腕时时酸痛。性子也越来越慢了。一回家母亲就说她:这孩子,怎么啥事都不着急。
部门和科组领导会委派年轻人做力所能及的修复工作。2013年联合国总部装修,罗涵参与到1970年代中国赠送给联合国的象牙雕作品《成昆铁路》的搬运项目中。《成昆铁路》由8根象牙组合而成,雕刻特别精细,稍有不慎就可能出问题。罗涵负责材料加固。“这种机会别人不会有啊!”她藏不住得意。去之前压力也是极大,“特吓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有时她也晚睡,为了写镶嵌文物的相关论文或修复报告。她必须花时间积累经验。她还没到外面去讲课,阅历、积淀都不够,“积累比假装更重要。”
罗涵毫不犹豫地夸起自己修复过的宝贝,“虽然在当时屏风很普通,就是一个日常用品,但它背后工艺不普通”,和当下作品最大的差异在气场:罗涵见过一只如意头——多层镂空工艺的玉雕上有一只正在飞翔的白鹭,四周连枝缠绕,第一眼就被震住了,“造型非常有风骨。”不像现在一些作品有形没神,罗涵看到的古物是“神形兼备”。她常常能感受到手中器物的制造工匠“有非常高的美学追求,手工工艺非常高超。中国古代工匠不像西方雕塑家对人体骨骼理解深刻,但古人做的东西有风骨。不像现在有些东西只有肉,没有结构感觉,没有任何力气,特别软”。
每天早上8点,罗涵从东门进入故宫,外面的声音啪地被彻底关上,只有跟鸡一样大的乌鸦在头顶嗷嗷叫。她穿过太和门广场,再走过断虹桥和一片银杏林,前后15分钟,她逐渐获得平静和思考。某种程度上而言,故宫里外的世界截然不同,外面在变,故宫文物科技部固守的是不变。“反正也不用跟着未来走,你不必害怕变化对你的影响。可以不惧未来。”罗涵说。
谈起故宫,罗涵陷入长久的沉思。记者建议先聊聊她喜欢的故宫角落,她大大松了口气,描述起春天的故宫文华殿前开的海棠花很美。忽然她的回忆就荡漾到接触文物的时刻:沉浸于巨大的美感,对比之下,许多事算什么呢。
在她看来,追寻心里头最想要的,才是事。比如去瑞士看巴塞尔钟表展就很重要。此前她一直被各种理由拖着。今年她想,为什么不去?为什么给自己找理由?“我就要单刀直入,就要去见它们。这是在故宫工作给我的力量,要突出重围。”结果3月她去瑞士的照片下面一阵点赞。她想,这些朋友假期比她多钱比她多,可没人迈出这一步。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我没有迷失,我反而更清晰了。”罗涵说。她也曾争先恐后,读书时特在乎奖学金、评级、争优秀。现在能跟那些浮动的欲望保持距离,“看古代人做的东西会有敬畏感,自己小小的情感并不那么重要。”
举重若轻,活在此时此刻
故宫雕塑馆。一位姑娘拉着同伴,“走啦,我们去看国家博物馆,这边的展品只是毛毛雨。”
2012年,故宫已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每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的博物馆。去年6月13日起,故宫试行每日8万人次的强制限流。这8万人大多来自全国各地,老老少少由旅游团带着,从午门进去,再穿过中轴线,最后从神武门出去。相比三大殿门口积攒的人头,雕塑馆、陶瓷馆、钟表馆、珍宝馆人数寥寥。
在罗涵看来,中国百姓对文物的关注度不高,对博物馆认识也滞后。故宫的宣传也不同于台北故宫,后者将翠玉白菜、肉形石写在了宣传手册最显眼位置。“陶瓷馆我们没做什么宣传,但里面放了什么呀?鸡缸杯哎。放了永乐和宣德年间的青花!随便拿一件都超贵,都没有独立展柜。宋代五大名窑摆好几件,没人看。所有人跟我说到故宫看什么?我说陶瓷馆啊,三天逛不完,为什么不看?瓷母、汉代的陶品、唐三彩,一排放着,没人看。”总有人问罗涵到故宫看什么,罗涵反问对方:你做一下功课行吗?
文保科技部火了,罗涵早有预感。“这份工作太特别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科室老师问过她,为什么不去故宫其他部门?她清楚这个时代“完全崇古或完全创新都不可能”,“科技部是个古今相结合的部门,需要很多新东西支撑我的修复技术。”果然,这几年文保科技部在故宫的权重不断提高。
研究生毕业时研究新材料的同学纷纷涌向国外,唯有罗涵笃信中国传统工艺已经很优秀。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了解帮助罗涵建构了清晰的身份认同——关于自己是谁,她真的很少疑惑。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情感大部分时候不会引起同龄人共鸣。有一次她跟朋友说,上世纪法国女性设计师Suzanne Belperron作品中的刻面宝石镶嵌受到东方元素的影响,朋友一脸不懂。最近故宫正在展出俄罗斯著名金匠法贝热的装饰花卉,罗涵在微信上给我发了几张中国传统珠宝玉石盆景的图片,“有些地方不及我们清中期的工艺,你看,很美。”
她非常相信自己的工作,“10年之前故宫还没人关注,曝光后就完全不同,因为之前还没回到历史舞台上。我们太缺乏对传统的探讨了。大家都认为国外文化好,其实中国古人达到很高的高度了。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古人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我们自己不要。”她认为国内缺乏对学生的审美教育,初高中历史太多政治色彩,美术课也往往被大家忽略,学生很少直观感受到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美。
在故宫罗涵获得一把校准自己位置的尺子:你试着做遥远古人做的东西,你知道自己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出十分之一。她认为自己还谈不上是个匠人,“工作性质不同,手艺也够不上(匠人),还是个技工。”
修复者有修复者的命运。“你没资格、也没办法自恋。做的人比修的人牛多了,他们是创造,我们是修复。手里的作品已经在一个高度了,你怎么可能自傲?充其量对自己挺满意,有些人没看到这个高度,觉得自己看到的极限就是极限,但真实的极限远很多。”
3月18日,“两岸三院同人书画交流展”开幕,墙上挂着一幅临摹室陈露画的纸本设色画《蝴蝶》:一位穿着白色吊带的女孩,短发齐肩,蝴蝶停在她的手上、额前,还有的在她头顶飞。这是陈露创造的另一个罗涵。罗涵在朋友圈贴了这张图,写道,“感觉生命被延长了,谢谢陈露。”
故宫于她的意义也是,“跟文物在一起,生命被延长了。” 她实实在在感到自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你加入到历史中了。文物永远都在,你对它进行修复,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一笔。”
文物从过去走来,又拥有无尽的未来。取消了时间的禁锢,罗涵恰好是活在此时此刻。这些文物修复师,亦是如此。
如同导演叶君告诉我的,进宫两三个星期后,他才拿到拍摄这部纪录片的钥匙——当他看到大伙在打杏子,杏子烂了一地被蚂蚁啃食。他羡慕师傅们的举重若轻,“哇塞,这真的是国家一级文物吗?这么破。这些人真是高手吗?有些人还是啤酒肚啊。”
周末的星巴克极其吵闹。3个小时里情绪饱满、高亢的屈峰,忽然缓慢了一会,说起自己最喜欢故宫的一片银杏林,去年冬天雪来得早,满地黄色蝴蝶状的落叶,藏在特别好看的白雪里,金灿灿的。
然后他念起中央美院导师跟他说的一句话:“真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吃大苦,甘寂寞,耐长期。”
(责任编辑:杨少杰 UM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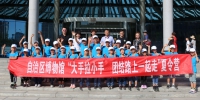


![APRZDJ%V$8P2MJ{]X88%6E4.png - 文化网](https://wulumuqi.baogaosu.com/content/image32367653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