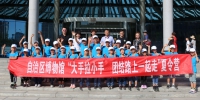新疆女诗人曾丽萍诗集:如风吹过的往事
曾丽萍简介:
曾丽萍,笔名如风。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诗选刊》《飞天》《诗潮》《诗林》《飞天》《安徽文学》《四川文学》《延河》《西部》《西北军事文学》《绿风诗刊》等多种报刊。部分作品入选《中国散文诗人》《2014中国年度散文诗》《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14年度诗歌》《中国,流泪的五月》《新疆新世纪汉语诗歌精品选》《新疆新世纪汉语散文精品选》等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那时花开》、诗画集《空中草原·那拉提》作品曾获“伊力特”杯全国诗歌大奖赛二等奖、“伊帕尔汗”杯全国诗歌大奖赛三等奖。系新疆作协会员、兵团作协会员、中外散文诗协会理事。
曾丽萍就像一首低吟的长诗,在天山北坡的绿洲和草原,静静地轻唱。她把自己血脉里的那些热情,把骨头里的那些精髓,把生活里的那些情义,提炼成一部低吟的圣歌,在我们走过的风里,悄然地回荡。她的诗,像一缕飘散在天边的彩云:恬淡、轻慢,蕴含着一种悠悠的诗情和画意,也饱含着一个女性诗人本质的真挚和温暖。
曾丽萍是从石河子市下野地镇走出的一个内敛、安静,不事张扬的女诗人。她把自己的笔名,命名为“如风”。她说:“一切的事物/我都无从把握//前世今生/悲欢离合/甚至窗外忽明忽暗的月光/和渐渐苏醒的春风”。她要把自己诗集的书名最初定为《路过》,这让我对她那淡然、虔敬和了悟的气质,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无论是“如风”还是“路过”,我都感到她对生活、对社会、对朋友、对诗歌的那种真诚的夙愿和执着的心意。
诗人曾丽萍是从自己生活的热土和文学的血脉里酝酿诗情的。她的诗,充满了内心情感的热血和女性视觉的色彩。她的坚韧和执着,她的美善和自爱,从她那一首首低吟轻唱的情诗,从她那一首首缠绵悱恻的怀乡恋曲,从她那一首首肝肠寸断的诗篇,就能清晰地看到那一个个鲜亮的节点。她的诗集《那在春天里走失的》,像一股温暖的春风,从我们的脸颊徐徐地吹来。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在诗集的第一辑《故乡,故乡》里,那深切的思念,缠绵的情意,隐隐的伤痛,让一个倔强坚韧的女子在行走他乡的路上,步履艰辛,心含隐痛。那一首首情深意绵的吟唱,是游子回首的泪花,还是肝肠寸断的怀念?
我怎么能够忘记,我的故乡——/那曾经住着父亲母亲的土坯房里透出的灯光/是我携带一生的温暖。我怎么能够忘记啊/我的故乡!那些记忆是扎在心头的一根刺/永远不能拔去,永远不能碰——《这些年我离你太远》
诗人对故乡的怀念,一直都是由父母住着土坯房透出的灯光照耀的,它温暖而又疼痛。这种怀念的美丽和伤痛,在诗人的心灵,蔓延和弥散,终于使诗人顿悟了自己“这些年我离你太远”的喟叹。诗人对父母和故乡的那种爱意的表达,由情至理,循序渐进。在《下野地的风》里诗人持续地抒发着这种感人的情怀:
下野地的风/陪着我在异乡漂泊/我不断回头张望那间斑驳的老屋/想躲回老屋温暖的屋檐下/下野地的风却又把我领到更远的地方
这是决绝的远离,还是一步一回首的告别?故乡的爱,也是故乡的痛,让诗人的心志更加的辽远,也让诗人更加的揪心。且看这首《最后的麦地》里的表述:
低矮的土屋有过昏暗的灯光/灯光下,母亲黢黑的面容曾让黑夜变得光明/斑驳的院墙里:黄瓜、豆角、翠绿的青春,热闹了袅袅炊烟/那扇饱经风吹日晒的柴门/目送着谁到远方寻找未来
诗人曾丽萍对母亲的怀念,一直被一间土坯房所环绕,被一道土坯房里透出的灯光所照亮。母亲的早逝,让诗人内心长久地隐藏着一种撕裂的内伤,这让诗人常常欲言又止。诗人的隐忍、慈爱、坚强和超然,可能与诗人父母的早逝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如果你了解了她的生活,就理解了她的诗歌;你理解了她的诗歌,也就当然读懂了她那淡然、恬静和忧郁的诗情。
当然,这一辑,也不乏轻盈欢快的诗歌:
雪,再也绷不住把持一冬的冷漠/一点一点地融化了/我也必须从一场冬眠中醒来/必须比一场春雨更早/赶在桃花开放前上路/
是的,桃花还未开放/我已经走在了探访春天的路上——《惊蛰》
惊蛰是万物复苏的节气,在春天里该如何用诗意表达自己的心情呢?是桃花盛开在温暖的心房,还是让妩媚的桃花染红诗人春天一样的心情?我们来看看她的《桃之妖妖》:
多么妖娆/野、枝头、嫩嫩的新绿/都敌不过桃花的嫣然一笑/是惊鸿一瞥的欣喜吧,顿时被你的妩媚/擦亮了眼睛——/
那轻轻浅浅的温柔/那慵懒而又随意伸曲的身姿/……/桃花,桃花——/你看春雪正为你融化/曾经多么坚硬冰冷的土地/也因你酥软了一颗心/醉倒在你盈盈的笑靥里
诗人的芳心,被桃花染醉。站在桃花摇曳的春天,畅想着春雪消融后的蓝天、白云和那绿草如茵的家园,诗人在用一个女性的温柔和视角,对桃之夭夭的春意,做一种诗意的畅想。这首诗,结构自然,情绪饱满,词义准确。整首诗在情绪的爆发,情感的表达,诗情的转喻上都浑然天成,像“酥软了一颗心”“盈盈的笑靥”,在诗情画意上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诗人在《桃之夭夭》写下不久,那春天里的桃花,依然冲动着她的情感,迷醉着她的芳心,所以“桃花的诗意”如泉喷涌,从而涌流成《芳菲四月》的诗行:“在春天的枝条上遐想/桃花就羞红了脸/藏了一冬的心事/经不住春风的询问/……/在阳光的陪伴下探春/春天就花红柳绿/四月天的芳菲啊/说着笑着就醉了行人的眼”。这是诗人面对桃花嫣然一笑的连续性定格,是一种美丽情绪的再次抒发。诗人的感情,汹涌而节制,像一支美丽的舞蹈,在我们的眼前,靓丽而过。
生活的逻辑,常常与诗人的思想逻辑是相悖而行的。我不知道这是生活有意要磨砺诗人的意志,还是要逼迫诗人在更加艰辛曲折的人生之路上更好地留下那深刻动人的诗篇?《那在春天里走失的》第二辑《光阴的画像》,似乎是诗人曾丽萍在凄然回首中,以隐忍的坚强,抚慰着伤痛的疤痕。那一行行诗句,是执着的沉思和踟蹰,也是浴火重生的渴望,更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奋起。整个诗歌的情绪,诗意的逻辑,像波浪的起伏:消沉——平缓——高扬,是一个“W”的情绪走向。
曾丽萍是一个充满热爱的诗人。不事张扬的内敛,让她的爱意,更具有纯粹的意义。执着的心力,坚守的情义,自持的操守,让她爱的路途漫长、曲折,从而充满悲壮美丽的色彩。她的《与君书》是这种悲壮、美丽的诗意喷涌:
此时不说苍茫与辽阔/不说千山万水的远/不说惊鸿般的相逢/也不说湿漉漉的离别//我想说我看见一只飞鸟/给天空留下的隐隐伤痕/我看见一棵香樟树孤独地遥望着北方//是的不说身边秋草枯黄芦苇浩荡/不说那天空苍蓝白云朵朵/这个午后你可曾看见/湘江水在我的心头/一遍一遍流过
这首诗,诗人在意境的营造,情绪的酝酿,结构的铺排,语言的表达上,都很见功底,是一首很美的诗作。
在《那在春天里走失的》诗集第三辑中,充满了诗人对于人生、爱情和未来的凝视、疑虑、追问和执着。诗人在跋涉的途中,险象环生,因此诗人不能不追问:“永远到底有多远?”
亲爱的我深深知道/每一条路都有尽头/每一个故事都有最终的结局/在我的内心深处曾战栗着/为我们的结局占卜/一遍遍地揣想永远到底有多远
——《永远到底有多远》
生活的严酷,人生的磨难,坚贞的守望,不息的追求,让诗人的心智走向从容、豁达和辽远。诗人在爱的跋涉中,警示着自己,也在警示着他人。诗歌,是诗人生活的轨迹,也是诗人心灵顿悟的一种释然。诗人通过自己诗歌的表达,似乎才会确认自己的感知。而女诗人的感知,可能更需要一种生活的追问和诗歌的追问才可能被最后确认。
诗人的情怀是细腻、开阔和冰清玉洁的。在生活的无奈中,常常也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外和惊喜。所以,这让我想起她的一首《誓言》的情诗,这是“伊帕尔汗”杯爱情诗大赛荣获三等奖的作品:
我就是那轮明月吧/那轮在你的波心悲喜交加的明月/如果你是滔滔的伊犁河//我就是那片紫色的薰衣草吧/仰望着你依恋着你的薰衣草/如果你是巍峨的天山/我就是那金色的麦田那灿烂的油菜花吧/幸福的憧憬着收获的季节/如果你是夏日里的阳光
当时光的河流把誓言带走/当天山脚下又萌生一片春天/我还是那轮孤独的月亮/是那忧伤的薰衣草/和空旷的麦田
当时光的河流把誓言带走/在被记忆遗失的远方/爱人你会不会听见/有一声呼唤/在那拉提草原久久不散
诗人的美丽,是在诗人诗歌的不停吟唱中日臻完美的。而美丽的诗歌,又是在诗人美丽的心灵浸润下结晶的琥珀。诗歌的魅力,其实就在于敏捷、准确地表达诗人那浓烈、厚重的感情。一个诗人在自己的生活里,最后能够坚守什么?能够坚守多少?这可能是由诗人对诗歌追求的意境决定的。因此,诗人在回望“那在春天里走失了的”过去,喃喃自语地说:
春天来了,春天真的来了/蓝蓝的天空,静静的田野/还有暖暖的春风暖暖地吹着/我们的约定却走失了/所有的爱和誓言走失了/
走失在这暖暖的春天里——《那在春天里走失的》
诗人在对往事的咀嚼中,对于走失在春天里的爱和誓言,往事和春雨,全都收进了自己的行囊,用一个女性的心志,包裹封存。她说:“我把关于这个夏天的一些片段/埋在记忆的坛中发酵/把一些恍惚的记忆和温柔/掩在心的荒漠//我把昨天的门轻轻关好/却忘了/给回忆上一把锁”。
诗人在她的《那在春天里走失的》第四辑里,则是一种走出冬天的雾霾,寻找明天太阳的心情。诗人在把昨天的门关上以后,走出冬天,在春的气息里静静倾听一座雪山的低语。她要寻找通往春天的曲径,她要沿着那条干涸的河床,翻越一片片的苍茫山峦,寻找家的路径。她说:
家
很远
很冷
我低头
向家一步步走去——《家》
诗人曾丽萍是一个爱家的女人,爱家的心情和心意,使她对自己的家,充满了一个诗人的无限热情。她精心地细细打点着自己的家,很累,很苦,但也很幸福。生活的厚重和艰辛,会使一个浪漫无邪的诗人坚强、自信和成熟起来,也会让一个诗人的诗歌纯洁、深刻起来。
在这本充满爱意的诗集中,那在春天里走失的年华、那在岁月里攀爬的脚步、那在风雨里漂泊的身影;那在回望中凝视的眼睛、那在咀嚼中体味的酸甜、那在回忆里驻足的思绪,林林总总地构成了一条无法忘怀的爱河:它纯净、强烈,不屈不挠,一往无前。亚里士多德曾说:“善是最高的美”,而诗集《那在春天里走失的》不仅仅是一个女诗人爱的絮语,还是善的慈航。所以诗人那在春天里走失了的,并不会是如风吹过的往事,而是爱与善的春风,是执着与坚韧的泪花,是明天冉冉升起的太阳,在向我们亲切地呢喃。我们多想诗意地生活在这美丽的大地上,可是生活总是严酷地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首先必须是热情、坚韧地坚守生活。(李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