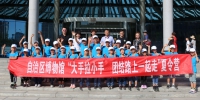袁运生:发挥壁画艺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桥梁作用
袁运生先生极为欣赏的库木吐喇新2窟菩萨。
袁运生先生极为欣赏的券顶菩萨群像(下)。
山东青州被称之为“永恒的微笑”的雕像(复制品)。
新疆日报讯(记者曹新玲报道)国庆节前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和新疆龟兹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丝绸之路传统壁画艺术研讨会”在地处克孜尔石窟的新疆龟兹研究院举行。
今年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一年,又适逢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新疆龟兹研究院成立30周年,可谓三喜临门。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召开此次壁画艺术研讨会,颇有纪念意义。
来自我国美术界壁画领域的著名壁画艺术家袁运生、刘秉江、唐小禾、李化吉等30多人围绕“龟兹壁画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与古丝绸之路的关系”“丝绸之路壁画艺术的传承、交流与发展”“如何解读和梳理龟兹及其其他古代壁画在当时和现今存在的意义”“如何使壁画艺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等话题展开了积极的交流研讨,气氛热烈。
会后,记者专访了作品等身、享有盛名,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创作北京国际机场壁画《生命的赞歌——欢乐的泼水节》开美术界思想解放风气之先、又去美国访学后回国从事美术教育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运生先生。
记者:袁老师好!很高兴你能接受采访。你是第一次来龟兹吗?对龟兹石窟印象如何?你如何看待龟兹石窟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袁运生:我以前来过新疆,来过龟兹,新疆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所以对龟兹石窟艺术的精美并不感觉吃惊。在龟兹,我不由感叹中国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感叹其恒久的魅力。相形之下,感觉现在的《中国美术史》很有必要补充许多内容,比如雕刻、比如青铜器,当然还有壁画,中国美术史对其都缺少一个系统的总结、系统的分析和归纳。过去我们写美术史,总参照国外的模式,但是我们与国外有不同的国情,是不同的国度,我们应该有自己编写美术史的方法,而这方面,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应该给予龟兹石窟艺术,包括青铜器、雕刻等艺术以应有的地位。
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去美国访学的,在美国,感觉其绘画、雕刻已经走向末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艺术发展是一种回顾式的发展,而美国是否定式的发展;中国是寻找到新的资源之后往前走,而美国总是否定后,继续重新建立新的体系。美国与中国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进步观。当时很失望,感觉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去寻找发展的路子,看能否寻找到新的促进中国美术发展的推动力。
“重建一个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这是我的心愿和努力方向。我们也正在做这一课题。经过摸索和努力,通过对中国传统艺术品的复制,我们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了寻找新的教材,我们一个省一个省的去寻找资料——我想,我们从教师开始就努力改变,给老师们以时间,让老师们先意识到重建我们中国自身的美术教育体系的重要,让他们熟悉和认可中国美术自身的价值,从基础部的教育开始抓起。
来龟兹其实就是一种寻找。
记者:你在发言中以龟兹壁画为例,屡屡提到考古、历史和美术艺术的关系,还多次强调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在美术创作中,坚守传统有多重要?
袁运生:是的,我特别想说说考古、历史和美术艺术的关系,考古学家的职责毋庸讳言,但考古与艺术结合有非常重要的价值,20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美术教材,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文明非常清晰的史料——但(也有这种情况),部分搞考古的人,不懂艺术,只要能把东西挖出来就行,写了考古报告就算完成任务了。若艺术家具备一些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在这中间就应该是座桥梁,艺术家应该取其(考古成果)中有价值的东西作为教材,很可惜就这样放过去了。
成为董希文先生(我国著名画家)的学生让我获益匪浅。先生非常中国化,非常坚守传统,而且画得非常成功。先生视野也很开阔,考古成果(文物),包括那些壁画、雕刻,先生都很重视,为我们绘画创作提供了新的研究学习对象……
现在,我们对中国文明的整体取舍和价值的把握还没有能力,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史料中寻找到更适合当教材的内容。像三星堆的
发掘,没想到三千年前的雕刻如此精美,而三星堆博物馆也对我们的课题非常支持,复制了10多尊雕像给我们……中国的青铜器之类也都非常精美,但我们缺少历史眼光,缺少辨识古代文物价值的审美能力,还没有深入发掘其中的价值。
我们所目见的不光是艺术品本身,而且应该是那件艺术品背后的东西。我们不能张口闭口说希腊罗马,我们应该有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关于这部分做得是非常差的——我们以前写的美术史太差太碎了,美术史只能叫绘画史,应该重写。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一方面要提供给美术史家资料,另一方面要弄教材;这件事非常重要(美术重要的是对教材的解读),我国西北、东北民间艺术非常发达,如剪纸手工等等,非常好,这样的东西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了,包括一些壁画、雕刻等,它们都是民间的工匠用心绘制、雕刻出来的,工匠自己是有他自己的积累的(口诀口传,人都逝去了,但口诀仍保留着……)这很难得。
我们丢失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我们唯有从作品来追溯绘制、雕刻作品的人,来追寻当时的作品创作已达到了怎样的水平。
一件大型作品肯定有两拨人在做,一拨人是理论设计,一拨人是能理解和掌握这些设计的工匠——当时他们是怎么想的,工匠们又是如何绘制、雕刻的,怎样将想法与材质结合起来的?我想,希腊罗马也应是类似的格局吧。
我们在山东青州复制了那座两尺多高的雕像(女像),那被称之为“永恒的微笑”的雕像。西方艺术家认为艺术品只能做到将要微笑或暂时微笑,很难做到“永恒的微笑”,他们一直在困惑,通过什么方式能把微笑这一美学难题解决了,但没有做到,可中国人解决了,而且无任何欠缺,难以想象中国雕刻竟然还有这么高的水平。
中国的许多艺术品完全超越了用西方思维(科学思维)难以解释的范畴。
探究中国雕刻解决美学难题的思路,可加深中国人对自己文明成果的重新认识,它解决的许多问题是西方没有解决的。我们现在看希腊雕刻,它说明性的东西太多,不像中国雕刻,既简练又传神。
记者:龟兹壁画的独特性到底在哪儿?你们的课题会将龟兹的内容纳进去吗?
袁运生:龟兹壁画跟内地壁画不同,有着它自己原初的清新、质朴,你从龟兹壁画一直看到内地壁画,会发现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唯有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才有可能将整个文明的轨迹,从初始到现在的状态,完整地保存下来。
新疆真是一块宝地。我真希望把那些壁画、雕刻从原地复制回来(担心它们因自然分化或人为原因而被毁坏),那样最好了。看这个新2窟(袁先生指着房间墙上镶嵌在画框里的库木吐喇新2窟壁画的临摹作品),非常精彩,既有独特的东西,又有自由在里面,像是没有完全描绘出具体内容,但想表达的意义已经到了。在大中国文化中,龟兹是不可多得的组成部分。而所说的不可多得,唯新疆、甘肃、青海、西藏这些个地方才有。
我们希望能和龟兹合作,将龟兹壁画作为美术教材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现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建构一个全新的美术教育体系上,这个工作量很大,需要花费很多精力,但它对有志于中国美术的学生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