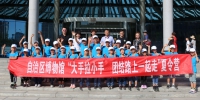“尧都”惊世考
二里头宫城东墙。(图片均由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室主任许宏提供)
■本报记者 李茂君 实习生 张嘉瑜
新闻背景
“陶寺就是‘尧都’,是我国考古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国都;陶寺时期是最早的‘中国’,其物质、精神和制度文明是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这一“文明探源”的新结论,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及山西省相关部门发起的几场研讨会公布,研讨会从去年年初开到年底,从临汾开到北京,传播甚广,跳出考古界引发社会持续关注,热议至今。
“尧舜禹”,“夏商周”,中华信史自何起?
1996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002年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九五”、“十五”连续组织大批专家、备受国内外瞩目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现在究竟对“中华五千年”有何新说法?
当山西陶寺“尧都之争”还在备受关注之际,记者首先前往13年前去过的另一地——2003年被冠以“夏都之争”的河南二里头遗址考古现场。
13年等于“零”?
还是13年前本报记者看过的那一排简陋的发掘物陈列柜,还是寒冷的田野,还是小屋饭桌,唯一不同的,是当年刚到此工作的小伙子赵海涛,现在升为了考古队的副队长。
13年,对队长许宏带的这批小伙伴们来说,青春已不复、风霜已满脸。但对1959年开始的二里头遗址发掘来说,57年来,几代考古人,也只挖了这里总共大约300万平方米的4万多平方米,也即1%多一点儿。
至于相对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更是一瞬。
二里头有一系列“中国之最”。在遗址现场,副队长赵海涛向记者介绍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车辙、最早的宫城“紫禁城”、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官营手工作坊区、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品读海量实物让人仿佛回到那个时期。
然而,13年前记者报道所说的“只有发现夏朝的相关文字才能证明有‘夏’。现在一个字都没发现”,至今依然没发现。就这点而言,13年是“零”。
这就是考古。
它需要严肃严谨的治学者、真心热爱的考古人,以及科学认真的考古氛围和社会认知。许宏和13年前一样,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对于有人“二里头近些年没什么进展”的诘问,认为考古好比“愚公移山”,科学审慎为要,作为探寻文化记忆、造福子孙的长远工程,不会也不应该是短期的形象工程,而应是一项“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长久事业。他从1999年接手到2006年,是一轮持续7年多的发掘,从2006年到2014年,编撰出版《二里头(1999-2006)》(5卷)又用了7年多,可谓“十五年磨一剑”:这是对新世纪以来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阶段性总结,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规制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也因此,许宏还一直很热心做一件事:自有博客、微博以来便笔耕不辍,将考古知识及时向公众普及,迄今已有博文近千篇,在考古界是知名的“公众考古实践者”。他笑言一来是自己建个“资料库”,二来方便让对夏商考古感兴趣的人查阅。经其精心编纂的《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先后问世,后者还入选“三联书店2014年十大好书”和当年的全国文博十佳图书。“这两本小书印了3万多册,在考古界很罕见。”这对许宏鼓舞极大,“我在书里介绍了二里头大量的中国之最,让大家知道这个都邑遗址在中国文明史上,有开创新纪元的历史地位。”
关于断定是否“夏都”,许宏依然是那个观点: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还是碳素测年、传世文献记载,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检核这一历史时段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绝对指标,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等狭义“信史”范畴的问题。就考古学而言,除了可以依凭的材料仍显不足,考古人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这种学术背景,决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结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断和假说的性质,某些具体结论,尚有待于更多证据的支持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如今,许宏甚至认为二里头可能是早商都城,但他认为没有必要急着“扣帽子”。
把二里头作为“最早的中国”阐释,是他的学术主攻:“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本身已经非常有意义,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为夏都。”在东亚大陆从没有中心、没有核心文化,过渡到出现高度发达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正好处于这一节点上。二里头的价值不在于最早也不在于最大,而是在这个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转折点上。从考古学本位看,他觉得足够了: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妨碍对二里头遗址在中国文明史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认识。
他期待一个贴近公众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公园和博物馆能尽快造好,至于博物馆名称,他反对加任何“X都”前缀。
那么,13年后,惊世的“尧都”又是怎么回事?
陶寺就是“尧都”?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上世纪50年代做全国文物普查时,这里有个龙山文化时期、面积超3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
1978年开始,本着寻找早期夏文化和“夏都”的学术目的,考古界对陶寺开始较大规模发掘。1981年,痴迷古文化的何努考入北大,专攻夏商周,其后师从该领域专家李伯谦攻读博士,2001年起成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领队及陶寺项目负责人。
去年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陶寺遗址出版了第一部发掘报告。考古界数十专家研讨,确认陶寺遗址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王国都城。也有一些专家笃定:陶寺就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北大文博学院教授、80岁的李伯谦说:“文献可贵之处就在于提供了线索。文献中记载尧都平阳,一种说法是在临汾,其古代就叫平阳,刚好在此发现距今4100年到4900年这一阶段的城,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尧的都城。”何努则认为,陶寺在汉魏平阳郡区域内,但不是平阳城。
何努对陶寺遗址的总体判断是:陶寺是“尧舜之都”,是最初的“中国”,陶寺邦国是中国文明核心开始形成的标志。他也笃定“尧舜禹传说时代”决非传说,是真实存在的“信史”。
“当时普遍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寻找早期的,考古所就把学术眼光往晋南,就找到陶寺。”何努介绍,早期挖掘成果主要有两大贡献:挖到普通居民区遗址和一片大墓地,分为早中晚三期,6个大墓中普遍有百余件随葬品,出土了龙盘、石器、彩绘陶器木器、少量玉器;40多座中型墓每个有几十件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剩下的占总数90%以上的小墓,一件随葬品都没有。
“这便证明了王权的存在,社会已有明显的阶级对立,金字塔式结构开始显现。”何努介绍,到1999年重新开始挖掘陶寺,目的很明确:不管陶寺是不是夏,先看陶寺是不是都城,进而探索陶寺文化是不是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都城,要有城墙、宫殿区、王陵区、祭天祭地祭祖的礼制建筑及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独立仓储区和普通民众居住区等要素,“经过十几年的辛苦,我们基本把陶寺作为都城的几个条件都找到了”。
挖掘发现,陶寺中晚期有个大的社会动荡,政权崩溃,城市和宫殿遭到严重破坏。何努认为这种摧毁是新政权对旧政权正统地位的否定和摧毁,表明整个社会进入了国家政治的状态,陶寺遗址体现出了文明和国家的形成。通过宏观聚落形态调查,何努发现陶寺控制的这个国家可能存在类似“都城-省会-县镇-村”四级行政组织,同时也发现了小型的驿站遗址,推测服务公务人员往来,这是中央和地方行政关系物化的表现。
陶寺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高度关注,一个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尽管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其采用合范浇铸技术,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还有一个是一把陶制扁壶,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一个类似于当下的“文”字,学界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有解读为“命”、“昜”、“邑”、“唐”等,何努认为就是“尧”字,“文尧”连起来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称颂。虽然数量不多,但何努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比甲骨文还早几百年。
何努要为“中国”重新释义。他认为词汇来源并非是传统认为的“中原之国”,而是“中土之国”。他的依据来自一个广受质疑的观象祭祀台,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圆心观测点有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何努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根据挖掘出的圭尺和圭表的测影演算,认为和《尧典》里记载的四表测量匹配,也和《周髀算经》里关于夏历冬历的影长数据吻合,确定陶寺就是“地中”,“中国”概念的来源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陶寺便是“最早中国”。
在天文学界,何努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认同。已故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成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
但天文学界的肯定并不能消解考古学界的质疑,多数考古人认为这种后人的先行假设再去论证还原,是“学术背叛”和不负责任“胡闹”。
对此,何努的师兄、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比较审慎,他说“挖到哪儿说到哪儿”是考古界的传统,如今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说到地基,至于地面上是什么及作何用,不能靠引申,还得有证据支撑。
记者发现,早在201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办方直接将陶寺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
虽质疑声不断,考古界对陶寺遗址的学术倾向性意见就是尧都,并且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去年,山西省和中国社科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个考古成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契合。虽争议仍然很多,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已足以“改写历史”。他表示,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文明起源向5000年靠近?
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于1996年5月正式启动,从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测定开始做起。
李伯谦介绍,按照史书记载,中国的“信史”是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在这之前的周朝早期和夏商,要么是传说,要么“有事无年”,于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重要课题,组织了相关领域专家,核心团队由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李伯谦、碳素测年专家仇士华、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首席科学家,组成不同学科的21人专家组,后扩展到40几人。断定年代以考古学为中心,挖出含碳的标本进行测定标出年代,还有就是依据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的年月日或月相等,再用天文历法推断。
到2000年9月结题时,该工程交出了“夏商周年表”。
李伯谦认为早期研究夏朝虽无文字古物验证,但可以文献史学为切入点,比如夏朝有14代17个王在文献上有记载,但具体验证得靠考古。
“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使商朝后期成为可信的历史,既然这段历史可靠,从盘庚往前推,夏朝乃至尧舜禹应该都是存在的。”李伯谦重视文献的“线索”价值,“所以夏商周年代的确定是以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年代的测定以及相关的文献记载为依据,是基本可信的。断代工程就基本完成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支持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2002年开始研究,到现在将要结题,试图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再往前探。
该项目也是以考古学为主,多学科合作,北大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两位任首席科学家,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组织,全国有几十家单位共同做。王巍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一些大命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
探源工程主要研究中国如何从基本平等的原始社会向复杂社会到接近国家社会转变,当时确定了黄河及长江流域的二里头、陶寺、良渚三大中心遗址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东北红山文化等重要遗址。
“进展非常大。长江流域以良渚遗址为代表,中原地区以陶寺为代表,是早期国家雏形。”李伯谦根据苏秉琦教授把原始社会到接近国家社会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看,帝国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从陶寺和良渚是方国阶段的开始,比它早的红山文化和河南铸鼎塬西坡遗址、安徽的凌家滩皆属于古国阶段。
良渚遗址距今4500年前,早于陶寺。在贵族的墓葬区有很多玉玺器,重要的玉玺器都有称之为神徽的图像——一个人戴着帽子手拿武器骑在神兽上的形象,这说明当时已有共同的信仰和崇拜。还有很多迹象表明当时阶级分化严重,最高的王墓葬中还有砍头的刑具,这些都是权力的象征。
尽管还没有确切追溯到5000年前,但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化的过程。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虽然有先有后发展不平衡,但三个流域都在同时演进,最后文明核心的形成是中原地区,西辽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后都衰落了。中原作为“熔炉”,直接影响到夏商周三代,这形成了中国文明和中国的主脉。从龙山晚期开始,以中原为中心的趋势开始形成,最早在晋南,出现了陶寺,然后是二里头,二里岗,直到殷墟,接上“信史”。
究竟如何?且先待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