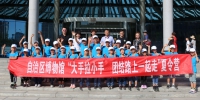锡伯人的“民歌精神” 一路欢声一路歌
李梅奶奶参加2013年察布查尔县组织的全国锡伯族民歌大赛,获得“锡伯族民歌王”称号。
李梅奶奶翻看其所著的《民歌》小册子。
陶晓梅、娜玉芳对唱锡伯族民歌。
天山网讯(记者李剑摄影报道)沿着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土路,记者来到了佟李梅老人的家。佟李梅是新近被公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锡伯族民歌的代表性传承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非遗干事郭金海在听闻记者要采访锡伯族民歌后,说,那一定得去听听李梅奶奶原汁原味的歌声。
如郭金海所说,李梅奶奶的家就像一个世外桃源,绿树红花,流水潺潺,甚是怡人。郭金海平静的语气里有对本族人所持的良好生活习惯的自豪:“锡伯人,无论家里条件好坏,都会把房子收拾得利利落落、干干净净。”记者认同他的看法。他们对待生活的这份认真态度,就像他们对生活保有的一份热情之心一样,都不会因为经济条件的好坏而改变。这一点,看一看他们唱锡伯族民歌时的神情姿态就能明白。
李梅奶奶一见到记者,就绽开一脸温和灿烂的笑容。今年79岁的她身体依然硬朗,穿着一身朴素干净的花衣裳,说起话来,声音也仍旧洪亮。她引记者进屋。一进门,一张贴在墙上、长达近两米的照片瞬间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79年10月2日,李梅奶奶指着照片说,这是当年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代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干部时的合影,并给记者指出位于照片右下角的她。作为锡伯族的民间歌手,她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她向记者介绍参与此次座谈会的缘由。1979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为了重新繁荣民间文艺,中央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艺座谈会,察布查尔县获得一个名额,就选派她去参加此次活动。
之所以选她是因为,此时她已经是全县内小有名气的民间歌手。对于这一点,老人家毫不谦虚,说:“1974年,县里文化馆招民歌演员,那么多人来唱,就数我唱得最多、最好。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我了。”
她身上有股热扑扑、坦荡荡的生活气息。记者愿意相信这是与其相伴一生的锡伯族民歌质朴、热辣、幽默的特点所赋予她的。这是一种深深地根植于土地中,根植于锡伯人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中的民间艺术形式。在佟加·庆夫和佟林清所编著的《锡伯族风情录》中,有这样一段介绍锡伯族民歌的文字:
锡伯族的民歌表现锡伯族的社会生活、生活习俗、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等内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出锡伯族人民的爱与憎、追求和向往。
按照内容和种类来分,锡伯族民歌可以分为叙事歌、苦歌、田野歌、情歌、习俗歌、劝导歌、渔猎歌、萨满歌等近十个类别,可以说,在过去的生活方式当中,锡伯族民歌贯穿了锡伯人的一生。
李梅奶奶回忆,她12岁辍学,开始学唱锡伯族民歌。1950年,解放军来了后,村子里成立了文艺队,15岁的她也报名参加。扭秧歌、划旱船、唱民歌,她样样来。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就不让在公开场合唱民歌了。但是,人们对于民歌的喜爱之情却丝毫不减。李梅奶奶说,大家在地里一起干农活时,常常有人对她说,李梅,唱首歌听听吧。她也不扭捏,应大家要求,一边干活,一边唱。“还有人会点歌。”李梅奶奶笑。她一边说着,一边就回到当时的生活情景中去了,坐在炕沿,轻轻点着脚尖,唱了起来:
我在菜地的这头,
姑娘在那头,
我想去跟你聊天,
中间却隔着菜田。
李梅奶奶唱得生动,歌词经郭金海向记者翻译过来,大有“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味道,但相比诗歌的文艺含蓄,它更有直露、奔放的坦率之美。这首情歌属于田野歌的范畴。田野歌是锡伯族民歌中曲调最为生动、内容最为广泛的民歌类别,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多以表现爱情为主。田野歌的曲调基本固定,歌词内容则可以根据对象和场合即兴编词。正如57岁的陶晓梅所说,锡伯族民歌就是眼睛里见到啥唱啥,脑子里想到什么唱什么。“西红柿也可以唱,葡萄也可以唱!”这个朴实的农家妇女指着桌子上的水果,咧着嘴笑道。她和52岁的娜玉芳都是堆齐牛录乡的文艺骨干,唱民歌,跳汗都春,她们都在行。记者在堆齐牛录乡文化站见到她们时,正是午饭时间。做了一上午的绣花鞋,她们正准备吃午饭。午饭是奶茶搭配从家里带来的锡伯大饼、烧茄子和菜园里的时鲜果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她们的眉眼就像她们所唱的民歌一样动人而温暖。这样淡然的日子也在歌声里变得可亲、喜人起来。她们唱:
树上的叶子已泛黄,
妹妹啊,
一边做鞋一边把哥哥想,
风儿吹得树枝儿弯下了腰,
多像妹妹在哥哥的肩头靠。
她们告诉记者,在这个乡里,凡是40岁以上的人都会唱民歌,大家一两个月就会聚一次,唱唱歌跳跳舞,平时逢了喜庆节日,也都要用歌舞助兴。就是在平日里,她们也是一边做鞋,一边唱歌。锡伯族民歌的率性自然,自由编唱,为锡伯人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
李梅奶奶就讲了一个发生在她生活中的有趣的故事。
30余年前,察布查尔县锡伯语言学会牵头组织察布查尔县与巩留县的锡伯族进行交流活动。当日上午,就有人告诉李梅奶奶,巩留县有个人要向她发出挑战,比赛唱民歌。下午聚餐时,两个人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对唱起来。渐渐地,他们被人群围在了中间,正式拉开了比赛的架势。最终,唱到十多首时,对方就没有歌能接了,自觉认了输,下了场。
记者问李梅奶奶,这么多年,有没有输过?
老人家一笑,唱歌还是以高兴为主,有时候还是要谦让一下的。
李梅奶奶著有一本名为《民歌》的小册子。她告诉记者,这是她早年收集整理的300多句田野歌的歌词。《民歌》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发行,说到整理歌词的缘起,朴实的老人也说得简单,唱了这么多年民歌,她也想自己套曲即兴编词。有了想法,她就一边唱,一边记录。也随之,她不仅记下了自己创作的歌词,也开始为流传在人们口头的田野歌词备一份文字记录。因而,诞生了这本小册子。
除了田野歌,李梅奶奶还向记者演唱了一首劝导歌。歌曲讲述的是一个吸鸦片的女人的生活变迁:我曾经貌美如花,如今却落得面黄肌瘦……劝导歌多是劝导人们摈弃恶习、从善从良的歌曲。李梅奶奶说,这首歌最早流传于鸦片盛行的清朝年间。彼时,奉命驻扎在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中也有很多人吸食鸦片。这首歌就是当时鸦片大行其道的一个缩影。如此看来,锡伯族民歌从另一个层面向后人讲述着前人的故事,为历史做了一个朴素的注脚。
与此相似的是,陶晓梅和娜玉芳所经历的与锡伯族民歌相关的往事。在她们那个年代,但凡姑娘嫁人,就必须要唱锡伯族民歌《丁巴歌》。何谓“丁巴歌”?陶晓梅解释得简单直白,即是男方为了让女方家里的亲友高兴所唱的歌曲。在过去,锡伯人的婚礼仪式隆重而复杂,婚礼常常要举行三天方可。第一天,男方向女方家里送彩礼和食品。第二天女方家里举行仪式。当晚,男方要派村子里5至7名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男性组成“丁巴”队伍到女方家里贺喜,并在宴席结束后与女方宾客分站两排,对歌跳舞,直至深夜。这个仪式过程被称为“打丁巴”。陶晓梅笑说,若是男方唱不好,就不给新娘子了。虽是这么说,打丁巴则重在热闹娱乐,倒是没有接不走的新娘。次日,新郎便在前方骑着高头大马,新娘坐在喜车上,一路向着新郎家而去。“丁巴”队伍则仍旧载歌载舞,尾随其后。锡伯族“打丁巴”的习俗具有“抢亲”的蕴意和抬高女方家地位的目的,据推测,这可能与古代氏族社会的“掠夺婚”和母系社会遗俗有关。
陶晓梅和娜玉芳出嫁时,也经历了这样热闹的婚礼场面,所不同的是,1976年结婚的陶晓梅出嫁时,有六匹马车来迎亲。到了上世纪80年代,娜玉芳是坐在汽车司机的旁边去往丈夫家的。
正如让陶晓梅和娜玉芳所怀念的这种热闹而有趣的婚礼场面在时隔多年后慢慢消失一样,现代的年轻人也多不会唱锡伯族民歌了。“他们听不懂,就不喜欢听了。”陶晓梅说。在她们的描述中,40,俨然一个分水岭。40岁以上的锡伯人,因为深深地体会过旧有的习俗、艺术所带来的乐趣和感动,所以对其仍抱有巨大的热情。而新一辈的人,则通过现代媒介与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甚少对古老的艺术形式产生兴趣。
如今,陶晓梅和娜玉芳都是李梅奶奶的学生。她们感慨,奶奶那么大年纪了,就在去年,还常常一个人从家里走很长的路到文化站来教她们唱歌。只是因为老伴去世,不宜出门,今年才一直待在家里。
我问李梅奶奶,等以后还参加活动、唱锡伯族民歌吗?
老人家说:“唱啊,我可是喜欢热热闹闹的场合呢!”
锡伯族民歌热闹而质朴。锡伯人的生活也是热闹而质朴。